治疗癌症的良药可能就隐藏在蜜蜂、蛇、螺类、蝎子甚至哺乳动物的毒素中...
死亡是促使我们关注有毒动物的第一驱动力。只要一想到没有四肢的蛇和脆弱的蜘蛛竟然能够战胜聪明强壮的灵长目动物,我们就会觉得既荒谬又可怕。不过,事情开始发生转变了。有毒动物也许会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20世纪90年代,约翰·恩格(John Eng)首次订购了一份吉拉毒蜥(Gila monster)的毒素样品。当时恩格还不太了解这种蜥蜴,因为他并不是专业的爬行动物研究者,而是纽约布朗克斯退伍军人医疗中心(Veterans A?airs Medical Center in the Bronx)的一位内分泌学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吉拉毒蜥真没什么好看的,这种蜥蜴体长近60厘米,原产于美国西南部沙漠,一直以恐怖著称。传言中,吉拉毒蜥咬住东西就不松口,只要被它们咬一下,就必死无疑。
事实上,吉拉毒蜥如今已被列入受威胁物种名录,是一种性情羞涩、行动缓慢的动物。确切地说,它们更喜欢待在地下洞穴里,因为白天洞里更凉爽潮湿。至于吉拉毒蜥的毒素,其实并不致命。和其他有毒物种相比,吉拉毒蜥可以说对人类基本无害,它们的毒性至少比那些著名的杀手弱100倍。当然,它们的毒素可能会让你剧痛难忍,但绝对无法轻松夺走任何人的性命。而恩格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医生治疗糖尿病的方式:这种蜥蜴的毒素中含有一种名叫艾塞那汀(exendin)的化合物。
订购这种蜥蜴时,恩格就已经想到了一些点子,他想鉴别对人体产生医学效果的未知激素。就在那时候,他读到了一篇报道,里面提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些来自有毒蜥蜴的激素会使实验动物的胰腺膨大,也就是说这种毒素或许能深度刺激胰腺,而胰腺是分泌胰岛素和其他关键激素的重要器官。恩格想方设法找到了吉拉毒蜥中造成上述效果的激素。在做了进一步检验后,他确认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多肽激素。随后,恩格将这种分子命名为“艾塞那汀”。
最终,恩格研发出了人造版的吉拉毒蜥毒素化合物,即“艾塞那汀-4”,他将这种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卖给了礼来制药公司。2006年,基于艾塞那汀的药物百泌达正式登陆美国市场。短短几年间,这款药为礼来公司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为了将百泌达与天然艾塞那汀区分开来,人造“艾塞那汀-4”又有了新的名字:艾塞那肽(exenatide)。艾塞那肽的作用类似胰高血糖素样肽-1(缩写为GLP-1),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帮助消化。艾塞那肽只有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所以和定期注射的胰岛素不同,这种激素不会造成意外的低血糖或“胰岛素昏迷”。更重要的是,GLP-1在人体内只能存在几分钟的时间,很快就会被分解掉。如果用它来做药,等不到起效就已经消失了,但艾塞那肽却能持续存在好几个小时。
对艾塞那肽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肽的“魔力”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20世纪90年代,美国衰老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的科学家在为艾塞那汀-4做临床前试验的时候发现,这种分子不仅能作用于胰腺,还会刺激神经细胞生长,延长成熟神经细胞的寿命。
吉拉毒蜥如今已被列入受威胁物种名录,是一种性情羞涩、行动缓慢的动物。
以毒入药
事实上,百泌达并不是“以毒入药”的第一个例子,作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药物,卡托普利(captopril)远远走在了它的前面。1981年,卡托普利获得了 FDA 的上市批准。这种提取自美洲矛头蝮蛇毒素的药物能够关闭一种重要的血管收缩通路,从而降低血压;另外两种来自蛇毒的抗凝药物依替巴肽(Integrilin)和替罗菲班(Aggrastat)也利用了蛇的血毒特性。如今,市面上共有6种提取自毒素的药物,而且我们对毒素入药的研究还很零散,几乎完全出于偶然。
“我认为毒素的潜力绝不仅仅是目前这几种新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格伦·金(Glenn King)表示。金教授最初是一位结构生物学家,他会利用核磁共振光谱法之类的复杂工具,借助原子的特性判断分子的形状和组成。某一天,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请金教授帮忙破译他在悉尼漏斗网蜘蛛毒素中发现的一种肽的结构。金教授对此很感兴趣,他问朋友要了一份样品。蜘蛛毒素庞杂的成分令他深感震撼。“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这真是一座无人过问的药学金矿。”从那以后,金教授一直在研究毒素,并从中寻找有用的化合物,无论是用来做杀虫剂,还是给人治病的药物。
几百年来,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用毒素来制药的想法。古代的中国、希腊和埃及都曾采用蜂针疗法,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历史记载被认为是完全不了解人体运作机制的古人误打误撞做出的正确选择。哪怕往最好的方向猜想,这些疗法也不过是民间偏方而已,它们常常和其他可疑的“疗法”一起被主流医学界嗤之以鼻。
19世纪结束时,一部分医生和科学家意识到,早期探索毒素的行动似乎蒙对了一些东西,于是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毒素的医学价值。此后,现代的其他毒素实验进展顺利。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蜂螫能改善多发性硬化的症状,蛇毒或许可以用来治疗关节炎。
例如,莱姆病是由一种螺旋形细菌引起的,病原体可能通过鹿蜱(肩突硬蜱)的毒吻进入人体。如果发现得早,大部分患者可以通过抗生素治疗轻松康复,但在某些情况下,出于我们尚不清楚的一些原因,顽固的细菌始终无法消除,最终会引发神经退行性病变。一位名叫埃莉·洛贝尔(Ellie Lobel)的女性就得了莱姆病,奄奄一息。洛贝尔拥有物理学背景,也是一位聪明的科学家,她告诉我,那时她已经病得动弹不得,几乎完全站不起来,脑子里也是一团糨糊,根本没法正常生活。她试了所有办法,但无论换多少医生,用哪种疗法,病魔总会卷土重来。
最后洛贝尔死心了,决定搬去加利福尼亚州等死。刚到这里没几天,埃莉就在出门散心时被一群非洲化蜜蜂(Africanized bee)蜇了。洛贝尔小时候被蜂螫过,当时差点因为过敏丧命,所以她认为这是命运在继续捉弄她。
此后,洛贝尔拒绝治疗蜂螫,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疼痛。但是,她并没有死。埃莉的疼痛终于开始消退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未来似乎又有了希望。谁也说不清是不是这些蜜蜂救了埃莉。但这个案例表明,“毒素救人”似乎不全是天方夜谭。很快她发现,蜜蜂毒素中最常见的成分蜂毒肽是一种强效抗生素,高剂量的蜂毒肽能撕裂细菌细胞并杀死它们。
更多的可能
与盲目使用毒素治疗疾病的的年代相比,我们已经对毒素有了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不仅知道是谁分泌了这些毒素,它们有什么效果,还知道它们是如何演化的,哪些成分最关键,以及让毒质得以大展神威的成千上万个活性部件。每一种毒素都包含着多种的成分,每一种成分都有专门的分子级目标,正是这样的特征让毒素成了制药学的宝库。
刚开始,科学家研究的只是那些毒素分泌量相对较大的动物,比如蛇。分泌量少一点的物种有蝎子和蜘蛛。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实际需求,因为在几十年前,分子级的测试需要消耗大量原材料。“过去十年来,技术飞速进步,”金教授表示,“现在我们可以用极微量的毒素完成筛查,这在过去根本做不到。”更让他欣喜的是,遗传学领域的进步创造了更多可能性。“现在我们可以从基因组学的角度审视这些动物的毒素,甚至不必真的去提纯毒素。”尤为重要的是,毒素拥有无与伦比的制药潜力。
可以说,癌症是天生的靶子,毒素已经瞄准了它。治疗癌症的良药可能就隐藏在蜜蜂、蛇、螺类、蝎子甚至哺乳动物的毒素中。2015年,抗癌新药SOR-C13完成了I期临床试验,离上市又近了一步。这是一种从鼩鼱身上提取的化合物。某些鼩鼱的牙齿上有特殊的沟槽,可以将这种强效的毒质送入猎物体内。与此同时,来自蝎毒的“肿瘤染色物质”BLZ-100刚刚开始I期临床试验。医生可以利用这种化合物鉴别癌症组织。医生希望,这种“染色物质”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儿童脑瘤手术。
某些最致命的感染也在毒素中找到了棋逢对手的敌人。最近,科学家发现,蜂毒的一种主要成分会攻击并杀死HIV,这种病毒每年都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150万人死亡。现在,科学家正在继续努力,希望由此为找到有效治疗艾滋病的疗法。与此类似,蛇毒中的一些化合物能有效对抗疟疾,这也是现代医学久攻而不克的一座顽固堡垒。如果这些发现真的能转化为新药,也许每年都能拯救上亿人的生命,缓解大量疾病患者的痛苦。
除此以外,毒素也许还能解决一些没那么要命的小病。巴西漫游蜘蛛(Brazilian wandering spider)毒素中的一种特殊的化合物,或许能够治疗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蜂毒的效果说不定比肉毒素还强,能够解决眼角的鱼尾纹;黑寡妇蜘蛛毒素中甚至还有一种潜在的杀精剂。
现在,除了其他几种有潜力的新药,金教授还在研究提取自蜈蚣毒素的一种止痛药,以及一种抗癫痫药。“我们之所以青睐节肢动物的毒素,比如蜘蛛、蝎子、蜈蚣,是因为这些化合物都是神经毒素,”他解释说,“这个庞大的分子库中充斥着可调节离子通道的各种化合物,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东西。”

39蜂疗网是中国蜂疗行业权威门户网,面向蜂疗专家、蜂疗医院、蜂疗从业者及蜂疗爱好者,提供传统中医学、针灸学、蜜蜂学、蜂疗学研究、技术、保健等领域的互联网线上线下服务。肩负“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蜂疗专业委员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蜂疗分会的国家级两大医疗学会秘书处工作”和蜂疗人才培养重任!
特别提醒:
1.本网收集的资料仅供患者与家属了解疾病与基本治疗原则、方法,具体治疗应遵医嘱。本网站内容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2、[39蜂疗网]在线专稿,转载请注明“39蜂疗网”。媒体合作请联系:010-87667632
本文来源:未知 ( 编辑:吴军)
标签:
已有 次访问,共0人喜欢 【我喜欢】

 蜂疗网
蜂疗网



 蜜蜂
蜜蜂
 蜜蜂
蜜蜂
 蜜蜂
蜜蜂
 湖南娄底蜂疗人 曾伟
湖南娄底蜂疗人 曾伟
 江苏如皋蜂疗人 刘红
江苏如皋蜂疗人 刘红
 江苏丹阳蜂疗人 陆九妹
江苏丹阳蜂疗人 陆九妹
 宣城市祥云养蜂专业合作社
宣城市祥云养蜂专业合作社
 宜黄远森蜂业合作社
宜黄远森蜂业合作社
 江西汪家养蜂场
江西汪家养蜂场
 蜂胶
蜂胶
 蜂蜜
蜂蜜
 蜂花粉
蜂花粉
 中国蜂疗抗癌第1人
中国蜂疗抗癌第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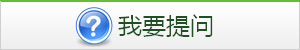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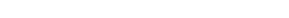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7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79号







